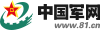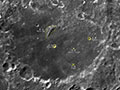夜 宿
“一出来,心全得放在车上,远方的家就顾不上了”
三十里营房,明月当空,星光闪烁。
驾驶室里,上士刘斐躺在车后座的铺上,和儿子文文视频通话——
“爸爸,你什么时候回来呀?”
“爸爸,你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?我等着你送我上学呢。”
面对儿子的追问,刘斐只能回答:“很快,很快……”
今年9月儿子该上幼儿园了,刘斐原本答应儿子开学时送他去学校。谁知,任务一来,他不得不“食言”。
“很快”,这不仅是刘斐、也是高原汽车兵,在路上哄家人最常说的话。
“一出来,心全得放在车上,远方的家就顾不上了。”刘斐腼腆地笑笑,“我也知道这样骗儿子不好,可不这么说又能怎么说呢?”
跑在这条离天最近、离家却很远的路上,当家里有事需要自己的时候,高原汽车兵脸上的表情是无奈的。
“咱爸住院了”“孩子又发烧了”“家里水管坏了煤气漏了”……四级军士长孔德明皱着眉头说:“相隔千里干着急、什么都做不了的感觉,特别折磨人。”
透过车窗,望着远处雪山上的圆月,中士李航心中涌起对爷爷的思念。李航从小跟着爷爷长大,有什么好吃的爷爷总是留着给他。爷爷去世的时候,李航正在去阿里边防送物资的路上。那天夜里,他一个人跑到戈壁滩上,朝着家乡的方向,流着泪给爷爷磕了3个响头。第二天一大早,李航把悲伤压在心底,和师傅一起开车继续前行。
“在路上,每个人家里都会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,大家都在坚持。”高原汽车兵们总感觉自己那么点事,“在集体里再普通不过,没什么可讲,大家都是这样挺过来的”。
夜深了,油机的轰鸣声戛然而止,全部的灯瞬时暗了。
和以往一样,上士赵振忠安排徒弟到兵站房间休息,自己睡在驾驶室里。
对汽车兵而言,车是另外一个家。
拉上车窗上的帘子,驾驶室后排那窄窄的座位就成了床;展开军被或睡袋,不足4平方米的驾驶室就成了汽车兵的家。
20岁那年,赵振忠可以独立出车了。这意味着他终于可以接车,也有了自己的“家”。
打开车门那一瞬,赵振忠的兴奋劲一下子被浇灭了——这是一辆已经服役17年的高龄军车,驾驶椅都快磨破了。
心里虽千般不情愿,但这毕竟是“自己的车”,赵振忠每天精心“伺候”这位“老伙计”。他记得师傅交代的话:“平时你不整车,关键时候车就会整你。”
3年前,这辆行驶60万公里的“老伙计”该退役了。冲洗、擦车、打黄油,“老伙计”的最后一个车场日,25岁的赵振忠将车里车外整得干干净净后,坐在那把磨得更加破旧的驾驶椅上,久久舍不得下来。
今晚,这个28岁的小伙子比平时睡得稍晚了一些。
中秋节快到了,他又无法陪妈妈一起过。车铺上的枕头,勾起了他的想家情绪——那枕头是母亲特意为他做的。7年来,这枕头陪伴他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昆仑山上的寒夜,带给他家的温暖。
夜更深了,兵站的军犬跑进车场,蜷卧车下,不发一声。车场后方,河水哗哗流淌,以不变的节奏奔腾而下。此时,整个兵站都进入了静谧的梦乡。
时 间
“这条曾经很陌生的路,成了生命中最熟悉最重要的路”
群山,望不到头。路上的回头弯,一个接着一个。
从红柳滩到多玛,300多公里,车队在颠簸中走了整整一天。
“现在路况好多了。”副政委孙晓亮说,“以往走这条路,没有最慢,只有更慢。”
那年,孙晓亮第一次“上山”,车胎爆了好几次。换一个轮胎,要拧10个螺丝。奇台达坂顶上,他和战友顶着风雪,忍着强烈高原反应,换胎时累得差点背过气去。翻越奇台达坂,他们整整用了一天。
那年,孙晓亮带队给边防连送物资。冻土消融,装满物资的军车仿佛跋涉在“奶油蛋糕铺成的路上”。车陷入泥坑14次,9吨物资装卸了9次。他们用了三天三夜,才抵达260公里外的边防连。
对于高原汽车兵来说,跑在这条路上,时间经常过得很慢——“遇到暴风雪、泥石流、山体滑坡,等待的分分秒秒都是一种煎熬”。
有时,时间又过得很快——指着驾驶员何其宝,孙晓亮笑着说:“还记得,这小子第一次上山,开车一下冲到护坡上!一转眼16年过去了,今年底他都面临走留了……”
听到这,何其宝也笑了,脸上却闪现一丝伤感。
今年底,34岁的何其宝就要退役了。一想到以后上不了山,他心里就会怅然若失。
16年,他从初出茅庐的愣小伙跑成了老汽车兵。这条路上,哪里有个弯,哪里有个坑,何其宝清清楚楚。被战友称为新藏线“活地图”的他,回到自己居住的都市却时常迷路,不得不用手机导航。
跑着跑着,“这条曾经很陌生的路,成了生命中最熟悉最重要的路”,成为高原汽车兵一辈子放不下的路。
退伍老兵尚志军新买的房子里,摆着一块普通的昆仑石。这块他视若珍宝的石头,是托战友从海拔5170米的奇台达坂专门带下山的。“看到它,就看到自己穿越昆仑风雪的青春岁月。”尚志军如是说。
喀喇昆仑的风雪,给每一个高原汽车兵留下了“终身印记”——
多玛兵站的深夜,参谋长曹正军的咳嗽声穿透墙壁,钻进大家的耳朵里。看到他咳得发紫的脸,没有一个人不感到心疼。“这么多年的老毛病,没啥事,挺挺就过去了。”这个跑了20多年高原的老汽车兵,挥着手回应着四周的关切。
“在这条路上跑,对身体的摧残起初没感觉,等有感觉时,问题就严重了。”作为团里跑高原时间最长的人,团长彭立勇的话像昆仑高原的风一样犀利。
高原汽车兵的工作节奏实在太快了——上山时,海拔从1000米升到5000多米;下山时,再从5000多米回到1000米。快上快下,缺氧醉氧交替轮回,生命在无形中加速损耗。
对此,他们早已习以为常。“习惯了”从他们嘴里第3遍说出来时,和第1遍没有什么两样。仿佛“习惯了”,就真的不苦了。
半夜,记者因高原反应醒来后,来到红柳滩兵站的停车场上透透气。整个世界是清冷的、安静的,只有风在这寂静的高原上奋力呼号。
没走几步,碰到政委朱彦杰夜巡。“因为这条路,我和战友们走到一起。也因为这条路,我和许多未曾谋面的老兵走到了一起。在这条寒冷孤寂的天路上,有我们高原汽车兵最热的血、最纯的情谊。”